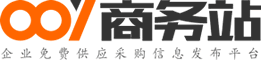随着暖季的到来,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抛开那些琐碎的烦恼,迎接奔向牧区参加节日庆典的欢乐时光。人们已经开始热议那场的百年庆典,而各省市县的新年拜访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这段时间,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似乎都被抛诸脑后,至少到秋天之前,我们可以享受片刻喘息。夏季的建设工程却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难题——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等到秋风吹起,沉浸在假日氛围中的蒙古人会猛然惊醒,难以割舍的节日余韵逐渐被愤怒和抱怨取代。人人仿佛一夜之间变得精明能干,针对所有不顺心的事互相指责,在拥挤的城市和建筑中争吵不休。
问题的根源,或许正出在“城市”本身。蒙古一半的人口都挤在首都乌兰巴托,城市的问题自然成了我们共同的难题。空气污染、交通拥堵、道路状况、供暖不足,再加上学校和幼儿园资源短缺、医院不堪重负……这些问题层出不穷,我们讨论过无数次原因,也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,但讨论仍在继续,似乎永无止境。
每当提到乌兰巴托的困境,历任市长总会抛出一句挡箭牌:“这座城市初是为40万人口设计的,现在有多少人挤在这里?”这句话一出,总是能堵住我们的嘴。现任市长赫·尼姆巴特尔和他的副手们这么说,前任领导们也如出一辙。那些曾经疯狂喊着“……我们的俄罗斯兄弟当年给我们建这座城市是大手笔,你们自己又干了什么?”的官员,如今倒是越来越少了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呢?难道要把40万“领导”留在这里,其他人统统赶出城?或者反过来质问: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,城市规划没有得到任何投资?为什么没能抓住重新规划的契机?这些问题同样尖锐。事实上,国家政策的失误和腐败对如今首都困境的影响显而易见。城市管理一直掌握在那些西装革履的官员手中,而非真正懂得经济和管理的人才。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,总是把所有工作交给“领导”——那些穿着昂贵套装、坐在办公桌后、与党派关系融洽的人。这种观念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根深蒂固,绝非虚言。如今,谁都能看出这种党派中心化的弊端依然存在。
管理一座城市,根本不需要这些衣冠楚楚的大人物。真正的城市管理团队应该每天从接收出生和死亡报告开始,忙碌到深夜解决问题,没有其他捷径可走。新闻部门也不该坐在玻璃大楼里,靠拨款给几个网站了事。乌兰巴托的所有困难,都是六十多年来管理失误的恶果——为了政治利益、党内表现,穿昂贵西装、开豪车炫耀成了常态。
其实,城市人口增长本该是市长们的骄傲。人口增加意味着城市经济壮大、能力提升,这在全球城市文化中是值得庆祝的事。新生儿出生时收到市长送来的礼物,整个产科医院洋溢着喜悦,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地方司空见惯。可在我们这里,人口增长却成了愤怒的。市民们也跟着烦躁起来:“外地人离我们远点,城市变成这样都是你们的错!”指责声此起彼伏。
但仔细想想,我们真正该做的,不是责怪从牧区来求学的学生,而是为更多人提供教育和知识;不是关闭市场,而是打造更多化、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市场;不是限制汽车,而是让更多车辆上路……这些才是世界城市的常态。因为随着这些增长,城市建设也会随之进步。市长们总不会说,北京早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就被规划成容纳3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吧?它可能初只是一个聚居地,逐步发展壮大。人口增加带来道路和桥梁的修建,住房和供暖设施的完善——城市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我们也该如此:扩大城市规模,容纳更多人口,每天铺设道路,让市民自由工作。只有这样,才能克服当前的困境。这对城市来说,本应是日常。
当然,的难题并非市长赫·尼姆巴特尔一人造成。认识到这一点,我们或许该停止对如今努力工作的年轻人泼冷水。新年伊始,蒙古国总理鲁·奥云额尔登推出了“乌兰巴托市2040年发展总体规划”,并在国家大呼拉尔发表讲话。希望有人认真听进去了。
城市是个活的有机体。参与制定乌兰巴托总体规划的专家们建议,要像提升身体免疫力一样,全面解决首都的问题。总理近也表示,世界上没有的好坏城市,只有规划是否得当、能否成功实施的区别。他呼吁达成共识,避免将首都问题政治化。这番话,显然是在剖析过去与现在后得出的
为支持首都基础设施发展,已成立由人士、规划专家、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,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推进工作。总理还感谢那些响应税法修改政策、投资空气和环境污染项目的私营企业,并呼吁更多企业加入。私营部门的反应却冷热不一。有人抱怨:“这算什么?给了我们什么机会?执政者似乎偏袒一部分人,对其他人只有拆除和破坏的‘礼物’。”这话不假。有些公司曾依法申请土地,甚至在拍卖中投入巨资,却因利益集团的压力15年来无法动工,无人赔偿他们的损失。另一部分人则愤怒地表示:“当年土地没人要时,市长亲自上门请大公司投资建设,承诺全力支持。如今却把所有责任推给我们。”这也是事实。
我们缺乏现成的经验,错误和腐败在所难免。
乌兰巴托发展总体规划于1954年获批,此后在1961年、1976年和1986年多次修订。直到2002年,才批准了“乌兰巴托市2020年发展总体规划”。2013年,国家大呼拉尔又通过决议,审议并批准了2030年的发展趋势文件。这些规划在国家政策中究竟有多大优先级?总理鲁·奥云额尔登指出,过去规划未能落实的原因包括:能源价格未及时放开,导致非规划区域的无序建设;治理不稳定,纪律松懈,非法占地泛滥;预算和投资不足,问题积重难返;缺乏问责机制;土地分配过多受政治决策干扰。
这次的“2040年总体规划”以可实施为原则,基于“20分钟城市”模式,从七大领域重新规划,借鉴国际经验,力求解决过度集中和发展失衡问题,打造环保、可持续的城市模式。项目包括沿图拉河建设32公里4-6车道快速公路、在Hui Doloon Hudag打造容纳3万人的新那达慕综合体,以及连接市中心与新卫星城的62.5公里垂直轴线高速公路。这些规划预计将高峰期车速从9公里/小时提升至22.5公里/小时。
工作已经启动,但坦白说,每次写到这些规划和政策时,总有批评者连看都不看。对他们来说,这太“无聊”。其实,我们不该如此。比如,为减少汽车依赖、提升公共交通,已规划沿和平大道建设17.7公里的地铁一、二号线,融资工作已提上日程。可我们却一知半解就成了“专家”,对一切指手画脚。
蒙古国虽地广人稀,但60%以上的居民挤在污染严重的首都。宪法赋予我们“在健康、安全环境中生活”的权利,可现实中,这权利几乎落空。70%的企业和组织也集中在乌兰巴托。为缓解这一局面,需支持地方发展,建立新定居点,制定可持续的人口政策。这是当下政策制定者的共识。
人口向乌兰巴托集中,已成城市发展的大阻力。研究显示,牧区到城市的迁移不会减弱,这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。所有梦想都指向城市,古今皆然,未来亦如此。不仅蒙古如此,全球城市化趋势都在加剧。各国通过更新规划和去中心化政策,扩展定居区域来应对。
是时候停止抱怨“城市初是为40万人设计的”了。1926年,乌兰巴托成立时拥有70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强大团队。如今,人才短缺却是大瓶颈。制定城市规划需10-15名工程师和建筑师,而全国范围内,拥有城市规划和经济学的双学位的人寥寥无几,这怎能不令人感慨?